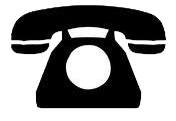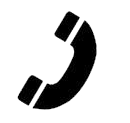倾听时代声音,从“善政”走向“善治”
2014年04月30日 来源:沂蒙人 2013年第6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呼吁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对任何执政党而言,倾听时代的声音是第一位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多个方面的历史性突破,而有关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提法更加引人瞩目——除了耳熟能详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外,还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其中。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就是倾听时代声音的结果。
在全世界的关注中,中国改革再次行进到“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紧要关头。当改革蓝图渐次铺开、改革期待点燃全社会热情,靠什么破解发展难题、化解风险挑战?靠什么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公平正义?靠什么约束权力、臻于善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无疑是撬动这些繁重任务的“总支点”。 国家治理的水准,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的科技和经济,更需要现代的政府和政党;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不仅是器物和工具的现代化,更是制度和治理的现代化。
治理的权威实施主体除政府外,还包括公共机构、经济组织、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善治的深刻意蕴就在于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就是一个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的过程。若没有这一过程,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治理与善治的提出并不是降低国家或政府的作用,而是主张对国家进行重新设计与建构,使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重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治理的过程更加离不开国家或政府的作用。
在由善政迈向善治的过程中,政府要能真正有所作为。这就要求政府不仅通过及时的自我变革,实现自身的内部结构优化,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挑起治理与善治的“大梁”。还要放下身段,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合作共治,以一个服务者的姿态,努力培育治理主体,从而为有效合作共治奠定基础。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单纯依靠政府,已无法解决好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治理与善治理论和实践的兴起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治理”一词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鲜明变化和时代性,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从根本上转变“万能政府”形象,并非易事。但是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必须跨过的难关。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束缚了企业、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容易出现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一些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的背后,存在部门利益的驱动。”少数政府部门的这一倾向已成为与民争利的根源。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能一视同仁,也会束缚社会资本的活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但占中国企业总数九成以上、总量突破千万家的民营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曾要求:“打破行业垄断,未来必须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放开市场准入,打开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天花板’。”
“推动政府自身改革,等于拿刀子割自己的肉,每走一步都不容易。”“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晒“三公”经费细账、推官员财产公示、减并政府机构、打击贪污腐败……面对一个个“硬骨头”,改革期待进一步突破。
随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开启大幕,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下放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公司注册资本“零门槛”、叫停公款考察性出访、大力度反腐倡廉……诸多改革释放出调整利益动真格的攻坚信号。
正如《决定》中所强调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进行了7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核心内容基本没有变,一直在围绕“机构、职能、人员编制”进行。而行政审批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这直接考验政府简政放权的诚意。实际上,半年多来,本届政府多次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并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经济公开课”上再次强调要“简政放权”,不能让政府“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不住的手”。
“开弓没有回头箭”,转变职能的政府改革,彰显的是改革者“自我限权”的勇气。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这也是执政党继十八大上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表述后,再一次用力度更猛的词汇—“必须”—来表明推进这项改革的决心。
新一轮司法改革已箭在弦上。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随着社会剧烈转型,利益分化、纠纷猛增,面对暴涨的司法需求,正义的供应能力难以匹配,司法机关的公正度和公信力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质疑—每年全国人大会上,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报告获得的反对票、弃权票,远远高于行政、立法机关,则是明证。在法律界人士看来,我国司法改革需要直面的“最大问题”是受困于司法的过度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等体制性痼疾,我国司法官和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很差,进而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的领导模式是地方司法机关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司法机关的双重领导。但当上级司法机关与地方党委的意见不一致时,地方司法机关通常是听命于当地党委,因为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是归地方“块块”主管。这也是造成司法权“地方化”的体制原因。不仅遭受着外部力量的干涉,司法官和司法机关在独立办案上也受困于内部的过度“行政化”。我国法院审判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层级加起来有8个之多,在这样的层级之下,法官、合议庭几乎丧失了对其审理案件的决定权。此外,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案件内部请示与审批制度,也使得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几乎演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现象普遍存在且有愈加严重趋势。
看到了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诸多弊端,近年来,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人士不断地呼吁进行根本性的涉及深层体制性问题的司法改革,以重建司法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公信的形象。但过去几年,我国的司法改革仍深陷于各自部门主导的外科手术式的“技术性微调”的改革方案漩涡中。
因此中央《决定》有关司法改革的论述对一些被业界诟病好多年的那些‘老大难’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这次统统给予了正面回应。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新思路,直面司法机关审判权、检察权独立性差这一“总病根”,选取了“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这两大突破口,多管齐下,“疗伤治病”,以重建司法的公信力。
由于司法改革不仅涉及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还涉及与其他党政机关和部门以及地方上的利益平衡,因此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新一轮司法改革祭出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让人们看到了最高决策层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从善政走向善治都可以说是各国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势。对中国而言,它是实现中国梦的路径。走向善治,必须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须大力构筑法治化基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让法治思维深入人心,让人民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必须不断推进的民主化进程,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政府与社会更多平行互动、协同治理……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用善治孕育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美的现代中国。
在全世界的关注中,中国改革再次行进到“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紧要关头。当改革蓝图渐次铺开、改革期待点燃全社会热情,靠什么破解发展难题、化解风险挑战?靠什么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公平正义?靠什么约束权力、臻于善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无疑是撬动这些繁重任务的“总支点”。 国家治理的水准,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的科技和经济,更需要现代的政府和政党;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不仅是器物和工具的现代化,更是制度和治理的现代化。
善治: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治理能力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早在16年前,世界银行出版的《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就聚焦于治理问题。世界银行认为,“善治(good governance)”或“有效治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关键,而实现有效治理需要相应的治理能力。因此,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还提醒发展中国家:政府擅长的事情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扩大政府掌控的范围。而善治的关键在于做好政府擅长的事情,为了实现善治,首先需要确定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什么”,政府“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认识到政府不能做什么,恰恰是现代治国思想的智慧。治理的权威实施主体除政府外,还包括公共机构、经济组织、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善治的深刻意蕴就在于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就是一个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的过程。若没有这一过程,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治理与善治的提出并不是降低国家或政府的作用,而是主张对国家进行重新设计与建构,使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重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治理的过程更加离不开国家或政府的作用。
在由善政迈向善治的过程中,政府要能真正有所作为。这就要求政府不仅通过及时的自我变革,实现自身的内部结构优化,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挑起治理与善治的“大梁”。还要放下身段,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合作共治,以一个服务者的姿态,努力培育治理主体,从而为有效合作共治奠定基础。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单纯依靠政府,已无法解决好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治理与善治理论和实践的兴起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治理”一词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鲜明变化和时代性,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善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突出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还是如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搞清楚政府的边界,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去争干市场的活,要纠正一些不当的干预微观经济的做法,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从“管理”到“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从根本上转变“万能政府”形象,并非易事。但是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必须跨过的难关。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束缚了企业、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容易出现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一些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的背后,存在部门利益的驱动。”少数政府部门的这一倾向已成为与民争利的根源。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能一视同仁,也会束缚社会资本的活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但占中国企业总数九成以上、总量突破千万家的民营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曾要求:“打破行业垄断,未来必须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放开市场准入,打开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天花板’。”
“推动政府自身改革,等于拿刀子割自己的肉,每走一步都不容易。”“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晒“三公”经费细账、推官员财产公示、减并政府机构、打击贪污腐败……面对一个个“硬骨头”,改革期待进一步突破。
随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开启大幕,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下放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公司注册资本“零门槛”、叫停公款考察性出访、大力度反腐倡廉……诸多改革释放出调整利益动真格的攻坚信号。
正如《决定》中所强调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进行了7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核心内容基本没有变,一直在围绕“机构、职能、人员编制”进行。而行政审批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这直接考验政府简政放权的诚意。实际上,半年多来,本届政府多次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并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经济公开课”上再次强调要“简政放权”,不能让政府“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不住的手”。
“开弓没有回头箭”,转变职能的政府改革,彰显的是改革者“自我限权”的勇气。
善治: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
善治意味着政治权力需要受到制约,这就需要发展和完善法治。只有“法治中国”,才有“善治中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这也是执政党继十八大上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表述后,再一次用力度更猛的词汇—“必须”—来表明推进这项改革的决心。
新一轮司法改革已箭在弦上。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随着社会剧烈转型,利益分化、纠纷猛增,面对暴涨的司法需求,正义的供应能力难以匹配,司法机关的公正度和公信力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质疑—每年全国人大会上,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报告获得的反对票、弃权票,远远高于行政、立法机关,则是明证。在法律界人士看来,我国司法改革需要直面的“最大问题”是受困于司法的过度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等体制性痼疾,我国司法官和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很差,进而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的领导模式是地方司法机关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司法机关的双重领导。但当上级司法机关与地方党委的意见不一致时,地方司法机关通常是听命于当地党委,因为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是归地方“块块”主管。这也是造成司法权“地方化”的体制原因。不仅遭受着外部力量的干涉,司法官和司法机关在独立办案上也受困于内部的过度“行政化”。我国法院审判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层级加起来有8个之多,在这样的层级之下,法官、合议庭几乎丧失了对其审理案件的决定权。此外,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案件内部请示与审批制度,也使得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几乎演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现象普遍存在且有愈加严重趋势。
看到了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诸多弊端,近年来,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人士不断地呼吁进行根本性的涉及深层体制性问题的司法改革,以重建司法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公信的形象。但过去几年,我国的司法改革仍深陷于各自部门主导的外科手术式的“技术性微调”的改革方案漩涡中。
因此中央《决定》有关司法改革的论述对一些被业界诟病好多年的那些‘老大难’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这次统统给予了正面回应。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新思路,直面司法机关审判权、检察权独立性差这一“总病根”,选取了“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这两大突破口,多管齐下,“疗伤治病”,以重建司法的公信力。
由于司法改革不仅涉及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还涉及与其他党政机关和部门以及地方上的利益平衡,因此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新一轮司法改革祭出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让人们看到了最高决策层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从善政走向善治都可以说是各国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势。对中国而言,它是实现中国梦的路径。走向善治,必须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须大力构筑法治化基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让法治思维深入人心,让人民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必须不断推进的民主化进程,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政府与社会更多平行互动、协同治理……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用善治孕育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美的现代中国。
(孙明杰)